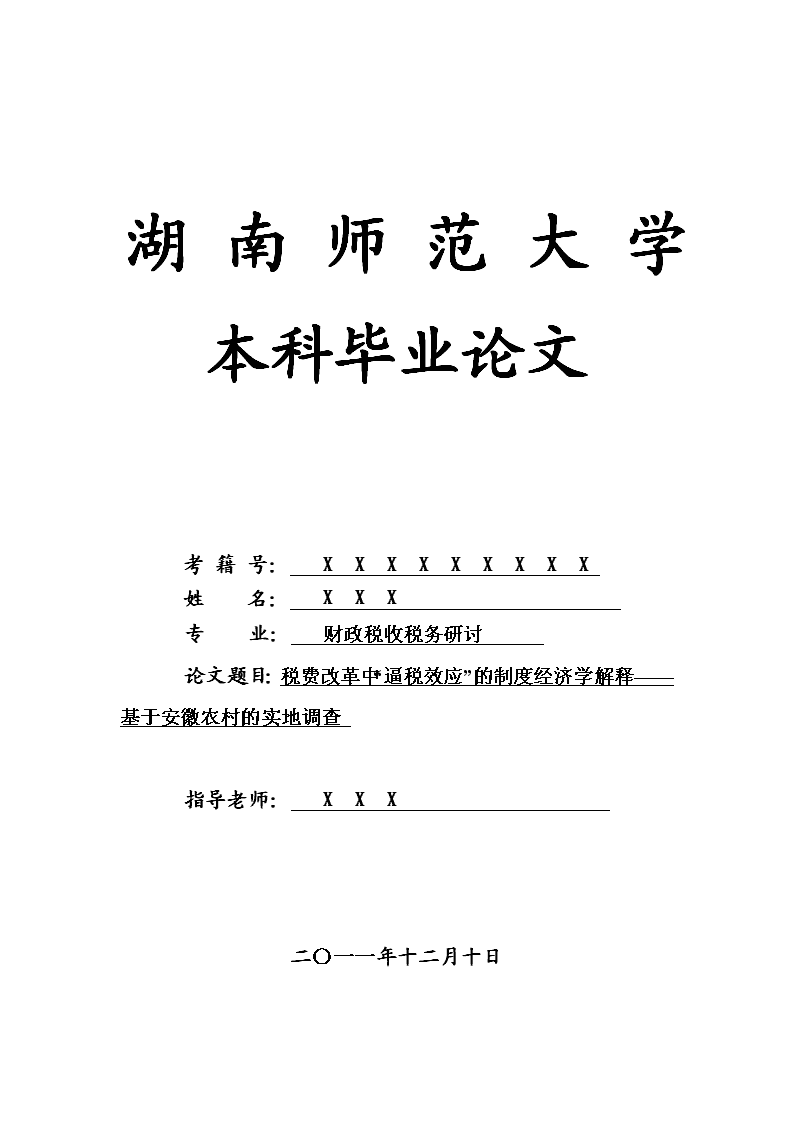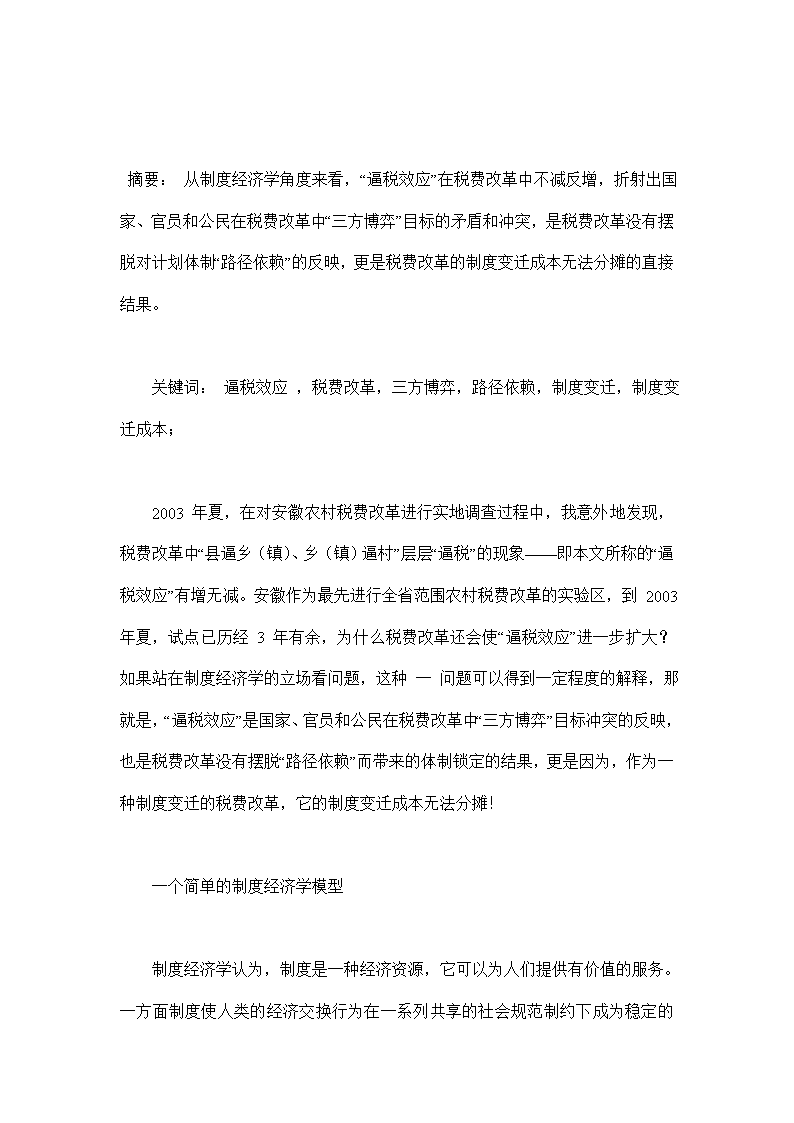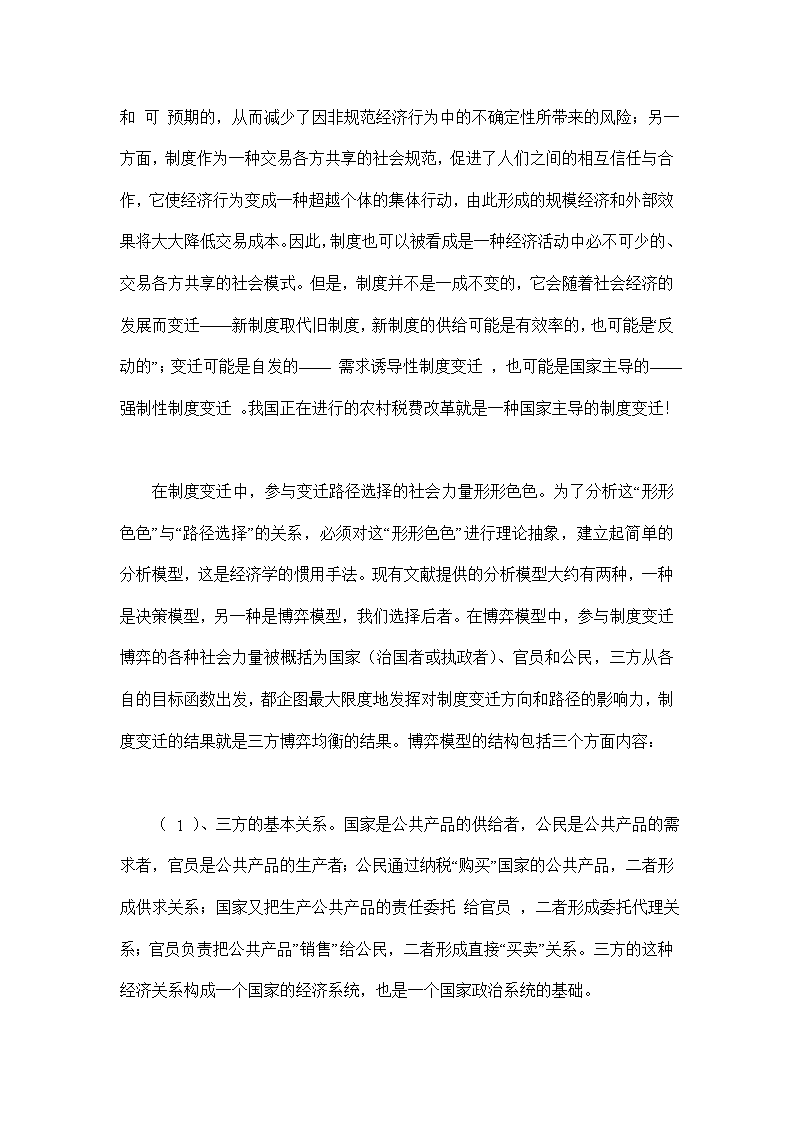- 46.00 KB
- 2022-04-22 11:48:31 发布
- 1、本文档共5页,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可选择认领,认领后既往收益都归您。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先通过免费阅读内容等途径辨别内容交易风险。如存在严重挂羊头卖狗肉之情形,可联系本站下载客服投诉处理。
- 文档侵权举报电话:19940600175。
'湖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考籍号:XXXXXXXXX姓名:XXX专业:财政税收税务研讨论文题目:税费改革中“逼税效应”的制度经济学解释——基于安徽农村的实地调查指导老师:XXX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日
摘要: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逼税效应”在税费改革中不减反增,折射出国家、官员和公民在税费改革中“三方博弈”目标的矛盾和冲突,是税费改革没有摆脱对计划体制“路径依赖”的反映,更是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无法分摊的直接结果。关键词:逼税效应,税费改革,三方博弈,路径依赖,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成本;2003年夏,在对安徽农村税费改革进行实地调查过程中,我意外地发现,税费改革中“县逼乡(镇)、乡(镇)逼村”层层“逼税”的现象——即本文所称的“逼税效应”有增无减。安徽作为最先进行全省范围农村税费改革的实验区,到2003年夏,试点已历经3年有余,为什么税费改革还会使“逼税效应”进一步扩大?如果站在制度经济学的立场看问题,这种一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释,那就是,“逼税效应”是国家、官员和公民在税费改革中“三方博弈”目标冲突的反映,也是税费改革没有摆脱“路径依赖”而带来的体制锁定的结果,更是因为,作为一种制度变迁的税费改革,它的制度变迁成本无法分摊!一个简单的制度经济学模型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种经济资源,它可以为人们提供有价值的服务。一方面制度使人类的经济交换行为在一系列共享的社会规范制约下成为稳定的和可预期的,从而减少了因非规范经济行为中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制度作为一种交易各方共享的社会规范,促进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它使经济行为变成一种超越个体的集体行动,由此形成的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将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制度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交易各方共享的社会模式。但是,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迁——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新制度的供给可能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反动的”;变迁可能是自发的——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也可能是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就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中,参与变迁路径选择的社会力量形形色色。为了分析这“形形色色”与“路径选择”的关系,必须对这“形形色色”进行理论抽象,建立起简单的分析模型,这是经济学的惯用手法。现有文献提供的分析模型大约有两种,一种是决策模型,另一种是博弈模型,我们选择后者。在博弈模型中,参与制度变迁博弈的各种社会力量被概括为国家(治国者或执政者)、官员和公民,三方从各自的目标函数出发,都企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对制度变迁方向和路径的影响力,制度变迁的结果就是三方博弈均衡的结果。博弈模型的结构包括三个方面内容:(1)、三方的基本关系。国家是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公民是公共产品的需求者,官员是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公民通过纳税“购买”国家的公共产品,二者形成供求关系;国家又把生产公共产品的责任委托给官员,二者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官员负责把公共产品”销售”给公民,二者形成直接“买卖”关系。三方的这种经济关系构成一个国家的经济系统,也是一个国家政治系统的基础。
(2)、三方有各自的目标函数。国家或治国者的目标函数是追求它的统治义理性的最大化,所谓义理性,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它“是‘符合命令——服从关系’的相应态度存在以及由此引发出与之相符的实际行为和二者相关程度的可能性”。通俗地说,治国者关心的是长治久安,尽可能持久而稳定地维持其政权的存在,尽可能扩大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所以,国家一方面希望通过提供物美价廉的公共产品和减少官员“生产”、“销售”公共产品过程中的“舞弊”行为以争取公民的拥护,另一方面,又得小心翼翼地呵护官员的利益,以尽可能多地取得官员的支持。公民则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得物美价廉的公共产品,他们一方面追求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又总是希望他们为此而付出的成本越小越好,即以最小的纳税义务换取最多、最美的公共产品。而官员们一方面希望国家不断扩大公共产品生产规模,以使他们的代理业务和寻利机会同时增加,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国家因超量生产公共产品而导致最终“破产”,致使他们失去“饭碗”。(3
)、制度变迁路径的选择是三方博弈均衡的结果。在制度变迁中,三方都必然要从自己的目标函数出发,各自考虑自己的利益,制度变迁又往往使三方的利益有得有失,这就决定着三方必然要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讨价还价,最后的各方妥协就是博弈均衡的结果。在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中,这种博弈依然存在,所不同的是,这时的博弈表现为国家与他方的主动结盟或合作;要使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最后成功,国家就要与公民、官员结盟,共同推动制度变迁,但由于三方利益不能完全相容,国家要想同时与另两方结盟,那是困难的;最好的选择是,国家在与官员、公民中的某一方结盟时,兼顾第三方的利益或给第三方较好的预期或承诺。在进行制度变迁分析中,不论是采用决策模型,还是采用博弈模型,有一点结论二者是一致的,那就是,二者都承认,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人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回头留恋张望”——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所谓“路径依赖”,是指制度变迁一旦在自我增强机制下选择了一条路径,它就会沿着这条路径走下去,也就是说,一次或偶然的机会会导致一种解决方法,而一旦这种方法流行起来,它会导致这种方法进入一定的轨迹。在实践中,人们看到的“路径依赖”现象会产生正反两个截然不同的效果,如果初始选择了正确路径,制度变迁就会在自我增强机制的作用下,使报酬递增普遍发生,经济、政治制度变迁会沿着初始选择的正确路径,进入环环相扣、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中,不断优化;这就好比中国人民在建国初正确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而在此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使各项事业全面蒸蒸日上。但是,如果那种路径依赖是“回头留恋张望”式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就意味着,制度变迁总是摆脱不了旧体制的惯性约束,从而使“路径依赖”成为制度变迁的障碍。人们常说的“路径依赖”主要是指这后一种情况。
要保证制度变迁的最后成功,不仅要克服“路径依赖”产生的不利影响,而且必须使制度变迁的成本有有效的分摊、偿付途径。制度变迁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人们期望取代旧制度的新制度更有效率,能够给人们带来更多的预期收益,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任何收益的实现都是要付出与其相对应的成本的,“没有免费的午餐”,制度变迁也是这样。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其变迁成本分摊、偿付往往是后移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轰轰烈烈,是因为革命者预期他们为“革命”做出的“牺牲”能够以“革命”胜利后的“幸福”抵偿,如果他们预期“革命”胜利后他们还要过“牛马不如的生活”,那么“革命”动力——诱导制度变迁的需求也就消失了,“革命”也就不可能发生。强制性制度变迁(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其变迁成本的分摊、偿付或者由“强制者”独立承担,或者后移,或者向外转移,如果没有给出制度变迁成本的明确分摊、偿付途径,那么,“强制者”就必然会遭到越来越多“被强制者”的抵制和反对,强制性制度变迁最终也就必将夭折!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就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在这制度变迁中,国家、公民(农民)、官员(主要是乡镇干部)的三方博弈正在僵持,路径依赖也有较强烈的表现,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无所出处已成为关系到税费改革成败的重要因素;而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从税费改革中扩大了的“逼税效应”那里找到它们的影子!税费改革中的“逼税效应”县、乡(镇)财税工作上表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税收任务逐级分解、下压,并把这种任务涂上浓厚的政治色彩,每年税收任务的完成都要求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负总责
、亲自抓,“一票否决”、“不交票子就交帽子”(完不成税收任务则乡镇一把手就有丢官的危险),这通常是县委书记、县长对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在财税工作上的通俗命令和“基本要求”;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则在无可奈何的表情下毫不犹豫地把这种压力转嫁给其辖下的乡镇干部和村委干部。农村基层干部把县、乡(镇)财税工作中的这种现象戏称为“逼税”,县逼乡(镇),乡(镇)逼村,年复一年。本以为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镇)财税工作将会旧貌换新颜;出我意料的是,农村税费改革后“逼税”更猖獗。2003年8月,我在安徽农村调研期间发现,农村税费改革后,“逼税”不仅使乡镇已有的矛盾更加突出,而且又在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上衍生出新的矛盾。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单兵突进,财政体制改革没有跟上,税费改革在原有的财政体制框架内运行,“逼税”的动因依然存在;于是,县委书记、县长们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给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们的命令又有了新的“说法”——“完成税收任务的办法我不管,税费改革的政策也不能违背,但分给你们的税收任务一定要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们就各显神通了;其结果是,农村税费改革不仅没有使“逼税效应”得到抑制,而且还使“逼税效应”乘税费改革的东风扩大了外延。具体地说,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的“逼税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逼税”使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走了样。要了解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是怎样走样的,你就必须要知道县、乡(镇)财税工作的实际操作——可不是你所知的理论规则。先讲县,县里的税收预算可不是遵循“量入为出”的原则,他们通常采用“以支定收”的办法,就是先“根据需要”匡算出今年的财政支出规模,然后根据这个财政支出规模确定今年的税收任务,并把这个任务分解到各部门、各乡镇,限期完成。各乡镇政府接受农业税税收任务后发现,如果“据实征收”是完不成任务的,于是各乡镇领导就琢磨起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来——因为县委书记要求税费改革政策不能违背;结果他们发现,根据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规定,农户应纳农业税税额等于计税面积、常年产量、计税价格三因素的乘积,而计税面积是根据二轮承包定下来的“死数”,计税价格是省里统一确定的,唯一可以由他们“因地制宜”的就是常年产量了。为了确保农业税税收任务的完成,乡镇干部们灵机一动想出了“反推倒算”的办法,他们先以本乡镇农业税任务数除以辖区内计税面积得出亩均应摊税额,再以亩均应摊税额除以计税价格,从而反推出“常年产量”,为了留有余地,他们还要把这个反推出的“常年产量”“适当”上浮后作为最后的执行标准,结果各乡镇制定的“常年产量”无一例外地呈现出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在我所调研的安徽某县,各乡镇制定的“常年产量”,最高的每亩960公斤,最低的每亩820公斤,而该县农民们的实际产量往往在每亩500公斤上下;显然,如此一来,常年产量失去了它“正常年景下平均产量”的本来意义,农民们当然就不满了。尽管如此,各乡镇总还有10—15%左右的农户农业税收不上来,怎么办呢?在“逼税”压力下,乡镇干部们又想出了“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好办法”;他们发现,农村税费改革后,农业税政策性强、“不好操作”,而农林特产税的“弹性”就大得多(安徽税费改革后的前三年农林特产税没有取消),于是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加大了农林特产税的征收力度;在我所调研的一个平畈乡镇,农林特产几近于零,而其征收的农林特产税却从税费改革前1999年的97万元增加到税费改革后2000年的103万元;农林特产税在承担起乡镇“补洞职能”的同时演化为“人头税”了。其二,“逼税”使乡(镇)、村两级出现了“税务”促“债务”的怪现象。众所周知,自1990
年代以来,乡(镇)、村两级债务居高不下,这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税费改革继续推进和农村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而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后“逼税”在继续,使这一潜在威胁正在逐步表面化。在当今农村,乡镇政府不仅要不折不扣地完成涉农税收任务,而且也要对辖区内国税、地税的征管负总责,同样是“一票否决”没商量,税务所(局)只是“技术性办事机构”;有税收征管权的税务干部没有必须完成的税收任务,而没有税收征管权的乡镇政府干部却要战斗在税收征管的第一线。县里为了强化这种“中国特色”的税收征管体制,通常都要对乡镇政府采取“激励措施”,在“分灶吃饭”的前提下,县里把自己的“以支定收”颠倒成“以收定支”,作为对乡镇政府的硬性约束;所谓“以收定支”,就是以各乡镇税收任务完成情况来核拔乡镇财政可用资金;比如某乡(镇)在规定期限内少完成税收任务2万元,则县财政就扣减该乡(镇)财政可用资金2
万元,甚至还要附加处罚;如果这个乡(镇)是需要吃转移支付的穷乡(镇),那就要从其应得转移支付中扣减。在这种压力下,乡镇政府一方面不得不向村里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就举债垫交县里的税收任务,同时村里迫于压力也举债垫交乡镇的税收任务。在我所调研的一个村,我“惊喜”地发现,虽然该村的债务规模不小,但其债务和债权却基本持平;它的债务基本上就是为按期完成税收任务而进行的举债,而它的债权就是那些应收上来但未收上来、甚至永远也收不上来的农户拖欠税款。除此而外,县里往往还不切实际地要求乡镇政府在完成税收任务时,要“按月均衡入库”,而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不到夏收或秋收时农户往往无钱交税,乡镇政府为了达到“按月均衡入库”的要求,就不得不举债垫交,这样,时差又使乡镇政府增加了利息支出。凡此种种的最后结果就是,“税务”促使乡(镇)、村两级别无选择地增加“债务”。当学者们在处心积虑地研究如何化解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乡(镇)、村债务危机时,恐怕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乡(镇)还是那乡(镇),那村还是村,那债已不是那债,而那“税”却就是那“债”。其三,“逼税”增加征税成本,越逼问题越多,形成恶性循环。在我所调研的农村地区,农村税费改革后,各乡镇党委、政府为了在政治上与上级党委保持一致——对于乡镇党委来说农村税费改革是上级党委交给的“政治任务”,实现上级提出的“坐征”(就是由农户主动到纳税点交税而不是干部上门收税)目标,同时确保税收任务的完成;各乡镇政府不得不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宣传动员的规模越大,则乡镇政府的业务开支也就越大;不仅如此,各乡镇政府还普遍采取了“激励措施”,对按期或提前完成农业税“坐征”任务的村按税收收入5%左右的比例给予奖励,对在规定期限前主动到纳税点交税的农户按其应纳税款的2%进行实物奖励——发放纪念品;同时组织人力在各村设“坐征”点,当然“坐征”点上也少不了一笔开支;“坐征”结束后,再进行评比,对税收任务完成好的集体和个人给予1000—2000元不等的物质奖励;几项合计,一个乡镇“坐征”的直接成本就占到其农业税税收收入的15%左右;结果党的面子是好看了,而农业税的征税成本却大幅度地提高了;更麻烦的是,这个成本县里是不予承认的,任务的“窟窿”就要由乡镇政府自力更生了。不仅如此,农业税上的“窟窿”还有,5%的社会减免之不足——交不起税的贫困户、不交税“钉子户”和杳无音信的“失踪户”(举家外出打工)一般占10%以上。同样的道理,乡镇的国税、地税任务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窟窿”。这样一来,如何填补“窟窿”就成了各乡镇领导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他们采取的最常用也是普遍的填补“窟窿”办法就是“买税”;所谓“买税”就是用乡镇政府自定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地纳税人在本乡镇交税,比如某税种的法定税率为5%,有一个乡镇政府向纳税人许诺在本乡镇只需交3%
,“交易”就能达成;但该乡镇向上级解递税款时仍须遵循5%的法定税率,这样,其中2%的差额就形成乡镇政府“买税”的价格,打入乡镇政府的征税成本。“买税”不仅造成国家税收收入流失,干扰了税收征管秩序,而且,对乡镇政府来说,“买税”也只能使乡镇财政危机延期爆发,因为“买税”虽然能填补乡镇政府眼前的任务“窟窿”,但“买税”价格却形成了乡镇政府未来债务。
其四,“逼税”动摇了农村基层政权,构成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农村税费改革后,由于“逼税”压力和历史债务的共同作用,使得乡、村两级空前困难。乡、村两级空前困难决定了税费改革后乡、村两级几乎无力向农村社区提供公共产品,这样就使乡村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和挑战,你没有能力“为人民服务”,何能成其为政府?更有甚者,有时上级政府向乡镇政府提供一点本应用于农村公共建设的专项资金,但乡镇政府迫于“逼税”压力,往往用专项资金垫交上级税收任务——即基层干部所称的“空转”,或挪作他用,这样就增加了人民群众的怨愤情绪。由于对乡镇领导者来说,“买税”和“空转”的政治风险都比较大,有些乡镇就用干部工资来填补税收任务的“窟窿”,结果造成乡镇政府干部工资长期拖欠;同样道理,许多村干部为了按期完成税收任务,就自掏腰包或举债垫交,村干部一个个变成了他人的债务人、政府或集体的债权人;“逼税”使农村基层干部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我在农村调研期间,一些村干部就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要不是让这些债权、债务弄得骑虎难下,他(她)们早就不想当村干部了;人们不想当村干部,再好的“村民自治”制度设计也必然流于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干部也是“理性人”,在他们经济拮据时忘记“共产党员修养”,是符合经济学逻辑的。农村基层政权是由干部组成的,农村基层的事要依靠干部去做。所以,对于农村社会稳定来说,上述现象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一种危险!何以如此呢?我们来尝试用前述制度经济学原理给这税费改革中更加猖獗的“逼税”现象找一找病根!税费改革中“逼税效应”的制度经济学解释客观地说,在农村税费改革前,基层的“逼税”现象即已存在。但“逼税效应”何以在税费改革中进一步扩大?很明显,“逼税效应”的扩大是税费改革中存在问题的折射;笔者认为,如果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逼税效应”在税费改革中有增无减,那是国家、官员和公民在税费改革中“三方博弈”目标冲突的反映,也是税费改革没有摆脱“路径依赖”的结果,更是因为,作为一种制度变迁的税费改革,它的制度变迁成本无法分摊!1、“逼税效应”的扩大是国家、官员和公民在税费改革中“三方博弈”目标冲突的反映。始于1978
年的“大包干”最初是由农民自发创造的,但很快就演变为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主要标志就是中央五个“一号文件”一步一个脚印地对“大包干”进行了引导和规范,最终使其成为“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此后,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三方博弈”的角度来看,这场变革之所以很快取得成功,是因为国家或治国者在推动这场变革时采取了“两手抓”的策略,国家一方面以“解放农民”为合作契约与农民(公民)结盟,充分满足了农民的利益要求;另一方面,国家主动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使地方官员及城镇的“一等公民”有了更多的利益,并对未来充满良好预期;如此结盟一方的同时兼顾另一方,使改革道路上的“反对”最小化。而正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国家在一开始发动农村税费改革时就把自己推向县、乡(镇)、村基层干部的对立面(税费改革面向农村,省及省以上政府在这场制度变迁中代表国家意志,所以此处“三方博弈”中的“官员”主要指县、乡(镇)、村基层干部,特别是乡(镇)、村干部,下同),国家发现基层干部无休止地加重农民负担,严重地威胁了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即我们常说的农村社会稳定,为了追求其统治的义理性,国家决定以税费改革的手段“减轻农民负担”,从而实现其与农民(公民)的结盟。但是,国家“减轻农民负担”是以向基层干部“开刀”为手段的,从税费改革实践看,禁止“三乱”、精简机构和干部分流、税费改革致使基层政府财政空前困难等无不与基层干部的目标函数相悖;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干部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攫取基层政府及其自身的利益,如不“合法”地积极“逼税”,别无他途。所谓农民负担反弹,只不过是“逼税”现象的变种而已,其差别在于,一个是“合法”的,一个是“非法”的。2、税费改革的“路径依赖”为“逼税效应”的扩大提供了条件。研究农村税费改革的各种政策和措施后,我们很容易发现,这其中的许多政策和措施在思想逻辑上和过去计划体制下的“干预、控制”思想暗合,表现出极强的“恋旧”情节,结果使税费改革演变为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农民、对农村基层组织、对农村社会控制力度的过程,充分暴露出农村税费改革没有摆脱对计划体制的“路径依赖”,而正是这种“路径依赖”为“逼税效应”的扩大提供了条件。其具体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1)、“费改税”是国家至上思想的沿袭,也为“逼税”提供了“法律保证”。农村税费改革又称“费改税”,它的主要特征是把过去具有“费”的属性的“三提五统”变成农业税附加,和农业税一道征收,这一下子使“费”国家化了——“费”有了“税”的“强制性”特征,国家或治国者以为,如此一来,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三乱”就乱不起来了,一切就好干了,殊不知这正是计划体制下国家至上思想的沿袭。我在农村调研期间发现,许多基层干部认为税费改革的好处在于:税改后,如果农民不缴“钱”,那就是“抗税”,可以对“抗税”者采取“法律手段”和“强制措施”。在他们看来,税费改革后,“逼税”已经有了“法律保证”了。(2)、“村财乡管”使政府实现了对农村基层组织的经济控制,也为基层“逼税”提供了动力和方便。农村税费改革的配套措施之一就是“村财乡管”,所谓“村财乡管”,就是依法征收的20%农业税附加由乡镇政府统一管理,而归村委会所有和使用,所以又叫“乡管村有”。这就使乡镇政府控制了村委会的经济命脉,使村民自治组织失去了经济上的自主权,实际上是对农村基层民主的“反动”。与此同时,“村财乡管”使得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乡镇干部和村干部经济利益“一体化”化了,使他们在“逼税”问题上保持立场一致;而且乡镇干部还可以通过“村财乡管”和“综合结算”的办法(村干部完不成税收任务则以其“村财”或村干部工资抵扣)来充分调动村干部“逼税”积极性。(3)、村干部“公职化”强化了政府对农村基层组织的政治控制,也为基层“逼税”提供了“组织保证”。
村干部“公职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税费改革后实行“村财乡管”,村干部由过去的“自己发工资”变成了“到政府领工资”,村干部和乡镇干部一样捧上了“铁饭碗”,有的地方甚至把“村财”纳入乡镇政府财政预算管理,村干部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公家人”了。二是在农村税费改革和乡村撤并、机构改革过程中,为了精简村组干部、减少村级开支、分流乡镇富余人员,政府将部分乡镇干部(也包括部分县直机关干部)下派到村级组织,担任村干部,并由政府财政负责其工资发放。据调查,安徽省五河县共选派209名国家干部下村担任村支部书记,全县只保留了16名农民村支部书记,每4—5个村派1名专业会计担任村会计,代管村级财务;长丰县也派150多名乡镇干部到村组织任支部书记,占全县363个行政村的41.3%。如此双管齐下,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村社会被牢牢控制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了,比计划经济时期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村民自治的载体岌岌可危。很显然,无论是前一种村干部,还是后一种村干部,他们都吃“公家饭”,当然就要“为公家干”,“逼税”也就不能含糊了。(4)、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强化了“对下控制”。为了克服农村税费改革单兵突进的缺陷,国家认识到必须进行与税费改革相配套的财政体制改革。为此,安徽省政府决定,在该省辖下的五河县进行县乡公共财政收支制度建设试点。主要做法是,以综合预算编制和管理改革为基础,以国库单一账户制度改革为重点,以预算统编、会计统配、国库统付、采购统办为主要内容,做到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一个口径,管理一个渠道,支出一个漏斗”。很明显,这种改革的通俗含义就是,财权上收、集中,强化“对下控制”,其结果必然促使农村基层干部进一步“对上负责”。因此,这种改革措施也就理所当然地无法遏止税费改革中“逼税效应”的扩大。
3、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无法分摊是“逼税效应”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原因。如前所言,税费改革作为一种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制度变迁成本必须有一个合理分摊、偿付的途径,才能保证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和最后成功。但是,和我国已经进行的其他渐进式改革措施一样,国家在进行税费改革决策时,更多地表现出“权宜之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过渡性特征,对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认识不足,结果不仅使税费改革本身举步维艰,同时也促使农村“逼税效应”进一步扩大。一般而言,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可采用变迁成本制度化、变迁成本由政府垫支、变迁成本向外转移、变迁成本向后推移等办法。令人遗憾的是,在税费改革中,这些办法要么准备不足,要么无法实行,结果迫使基层政府惟有走“逼税”之一途。(1)、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没有制度化安排、政府垫支不足。从现在的情况看,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主要包括三项,即因税费改革造成的县乡财政收支缺口、失去偿还来源的庞大乡村两级历史债务和基层干部分流的安置费用;由于税费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为了“迅速”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而采取的“应急措施”,所以对此种制度变迁成本的规模和分摊难度估计不足,更没有做完备的制度性安排。税费改革的改革对象是县、乡、村,垫支制度变迁成本的“政府”当然只能是其上级政府,当时中央确实考虑到税费改革可能会使县乡财政收支出现缺口,但就这一点也未做到位;以安徽省为例,2000年,全省各级政府因税费改革而减收13.11亿元,平均每县减收1542万元,当年中央财政向安徽提供的“税费改革”专项转移支付只有11亿元;
乡村两级历史债务和基层干部分流的安置费用则根本未予考虑。(2)、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被内部化,也无法向后推移。由于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不足以解决基层政府因税费改革造成的财政收支缺口问题,乡村两级的历史债务又要靠乡、村两级基层组织“自力更生”,被分流出去自谋职业的乡镇干部三年内还要在所在乡镇领取工资,且此后的一次性安置费用也没有着落,这实际上等于说,要基层政府负担税费改革制度变迁成本的绝大部分,即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被内部化了。除了乡村历史债务可以暂时赖着不还,向后拖一拖外,基层政府因税费改革造成的财政收支缺口和分流干部三年内的工资及安置费用这两项制度变迁成本都是必须即期支付的,因为向后推移即意味着基层政府的瘫痪!所以,有人说,税费改革使“农民笑了、干部苦了、乡村垮了”,制度变迁成本没有合理的分摊途径是其直接根源;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政府努力“逼税”尚且捉襟见肘,不“逼税”又当如何?【参考文献】[1]、邓大才,制度供给陷阱与农村税费改革[J],山东社会科学,2003,(3);[2]、张宇燕何帆,由财政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M],市场逻辑与制度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3]、张德元,我看农村第三次革命[J],社会科学战线,2003,(3);[4]、张德元,揭秘税费改革后的“逼税效应”[J],乡镇论坛,2003,(21);'
您可能关注的文档
- 财政税收税务研讨毕业论文 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doc
- 财政税收税务研讨毕业论文 税收立法若干基本问题探讨.doc
- 财政税收税务研讨毕业论文 税收竞争有害论质疑(一).doc
- 财政税收税务研讨毕业论文 税收竞争有害论质疑(三).doc
- 财政税收税务研讨毕业论文 税收竞争有害论质疑(二).doc
- 财政税收税务研讨毕业论文 税收遵从度的衡量.doc
- 财政税收税务研讨毕业论文 税权划分的理性思考.doc
- 财政税收税务研讨毕业论文 税负平衡点分析在增值税税务筹划中的应用.doc
- 财政税收税务研讨毕业论文 税负转嫁几个问题的再探讨.doc
- 财政税收税务研讨毕业论文 第一税案与财税法之补缺.doc
- 财政税收税务研讨毕业论文 筹资决策中的所得税 筹划.doc
- 财政税收税务研讨毕业论文 纳税人,说出你的权利[上].doc
- 财政税收税务研讨毕业论文 纳税人,说出你的权利[下].doc
- 财政税收税务研讨毕业论文 纳税评估制度的国际比较与借鉴探析.doc
- 财政税收税务研讨毕业论文 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税收竞争与税收优惠.doc
- 财政税收税务研讨毕业论文 缺失治理资源的乡村权威与税费征收中的干群博弈.doc
- 财政税收税务研讨毕业论文 网络经济对税收制度的影响.doc
- 财政税收税务研讨毕业论文 网络经济对税收的影响及对策.doc
相关文档
- 施工规范CECS140-2002给水排水工程埋地管芯缠丝预应力混凝土管和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管道结构设计规程
- 施工规范CECS141-2002给水排水工程埋地钢管管道结构设计规程
- 施工规范CECS142-2002给水排水工程埋地铸铁管管道结构设计规程
- 施工规范CECS143-2002给水排水工程埋地预制混凝土圆形管管道结构设计规程
- 施工规范CECS145-2002给水排水工程埋地矩形管管道结构设计规程
- 施工规范CECS190-2005给水排水工程埋地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夹砂管管道结构设计规程
- cecs 140:2002 给水排水工程埋地管芯缠丝预应力混凝土管和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管道结构设计规程(含条文说明)
- cecs 141:2002 给水排水工程埋地钢管管道结构设计规程 条文说明
- cecs 140:2002 给水排水工程埋地管芯缠丝预应力混凝土管和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管道结构设计规程 条文说明
- cecs 142:2002 给水排水工程埋地铸铁管管道结构设计规程 条文说明